
珠江之畔,琶洲国际会展中心的穹顶之下,人潮涌动,万商云集。今天大圣证券,2025年10月15日,第138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(广交会)如期拉开帷幕。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、混合了全球各种语言的商业气息,但细心观察,你会发现一股全新的潮流正在涌动,它预示着这座千年商都乃至整个中国对外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。

自1957年诞生以来,广交会便被誉为“中国第一展”和外贸的“风向标”与“晴雨表”。它几乎从未间断地见证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,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每一个关键节点。然而,今天,这个全球最大的“超级货架”正在悄然演变。除了琳琅满目的商品,思想、技术与资本的碰撞正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。其中,一场名为“新技术新成果”的发布会,虽然在广交会庞大的体量中只占一隅,却如同一声清脆的号角,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:一个将实验室的“书架”与全球市场的“货架”直接链接的时代。
广交会的历史坐标
——从“破冰之舟”到“世界商廊”
要理解今日之变,必须回溯广交会的历史长河。它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“破局”。在上世纪50年代,面对西方的经济封锁与货物禁运,新中国亟需一个窗口来与世界进行贸易,赚取宝贵的外汇。1957年,广交会在广州应运而生,成为一艘承载着国家希望的“破冰之舟”。在那个年代,广交会的成交额一度占据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。它不仅是贸易的平台,更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身、传递友谊的红色信使。
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南粤大地,广交会的角色也从唯一的“窗口”转变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强大“引擎”。它成为广东乃至全国企业“借船出海”的启蒙港口,推动了“广东制造”风靡全球,并为广东带来了大量的订单、外资和先进的管理经验。从最初单一的国营外贸公司唱主角,到后来民营企业、三资企业百花齐放,广交会展馆的每一次扩建与搬迁,都刻印着中国外贸几何级数增长的足迹。

进入21世纪,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,广交会再次转型,从单一的出口平台升级为进出口双向交流的国际公共平台。它不再仅仅满足于把中国商品卖出去,更致力于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,促进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。近年来,面对全球疫情的挑战和数字化浪潮的冲击,广交会又率先实现了线上线下融合办展的创举,展现了其强大的韧性与适应能力。
可以说,广交会六十八年的历史,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史。它的每一次进化,都精准地踩在了国家战略发展的鼓点上。而今天,当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从商品贸易更多地转向技术、标准和产业链主导权的争夺时,广交会再次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,开始了又一次深刻的自我革新。
平行时空里的另一条主线
——广东的“科创长征”
在广交会这条光芒四射的贸易主线之外大圣证券,广东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,也进行着一场同样波澜壮阔的“科创长征”。这条主线虽然在早期不如前者耀眼,却为今天广东的战略转型积蓄了最深厚的能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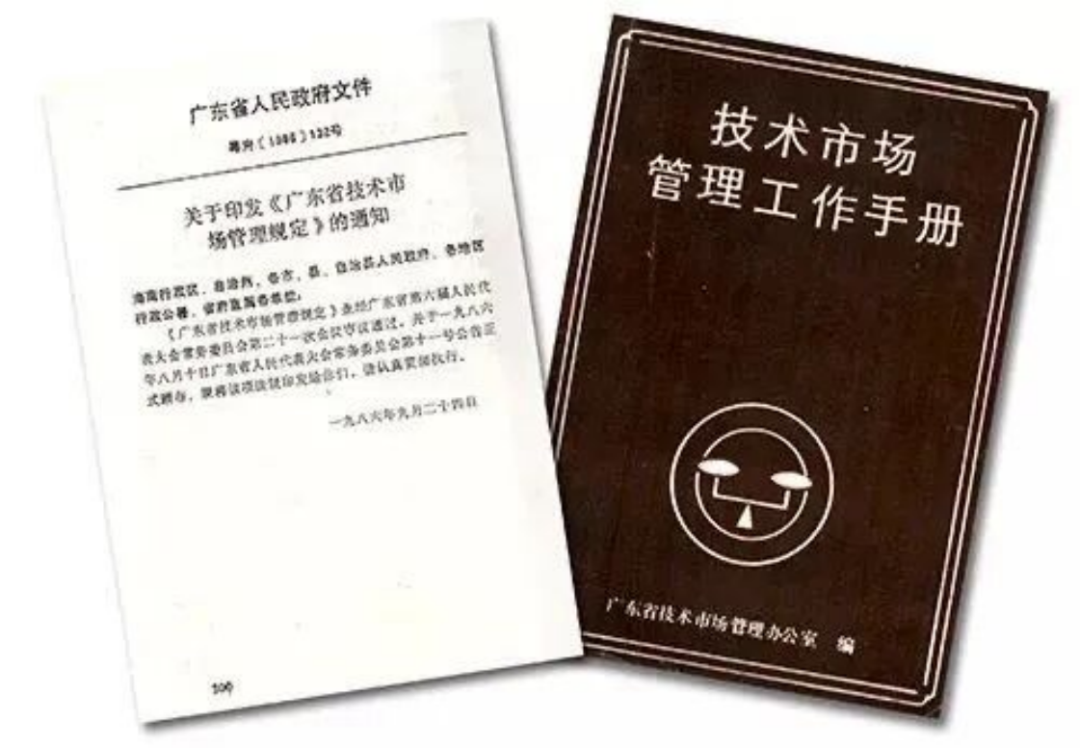
广东的科技创新意识,同样萌芽于改革开放之初。1981年,任仲夷在广东省科技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:“技术是商品,科研成果和专利也可以买卖!”这一论断直接挑战了计划经济传统认知。广东率先创新,允许科研机构与企业直接洽谈交易,并规定技术转让费可占销售额的3%-5%。首批交易的50项技术中,华南理工大学的“新型陶瓷材料制备工艺”被佛山建材厂以12万元购得,成为新中国第一笔市场化技术交易。1986年,广东颁布了全国第一部地方性技术市场管理法规,用制度的形式为技术作为商品流通打开了闸门。

进入上世纪90年代,当“广东制造”凭借“三来一补”模式席卷全球时,一批具有远见的企业已经开始在技术上默默耕耘。华为从代理程控交换机起家,毅然投入全部资源进行自主研发,最终在通信设备领域实现了对西方巨头的追赶与超越 。这成为广东企业从“制造”向“创造”转型的经典缩影。此后,中兴、比亚迪、TCL等一大批科技企业相继崛起,它们共同构成了广东创新驱动的“企业军团”。
进入新世纪,广东省开始系统性地构建区域创新体系。从2008年发布《广东省建设创新型广东行动纲要》,到近年来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,广东在研发投入、发明专利拥有量、高层次人才集聚等方面均领跑全国。更为重要的是,广东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布局“国之重器”,中国散裂中子源、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(“天河二号”)、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、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一批大科学装置相继落户。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平台。同时,鹏城实验室、广州实验室等一批高水平省实验室的建立,更是将创新的“策源”能力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。
这条长达四十余年的长征之路,让广东从一个技术引进的“追随者”,逐渐成长为部分领域的“并跑者”甚至“领跑者”。它为广东积累了雄厚的技术实力、完善的产业生态和一批世界级的科技企业,也为今天贸易与科技的“胜利会师”埋下了伏笔。
历史性的交汇
——当全球贸易“货架”
拥抱科技成果“书架”
2025年10月15日,在第138届广交会上,这两条看似平行的历史主线—贸易与科技,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交汇。在广交会现场的“新技术新成果”发布会上,来自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(粤港澳大湾区)的“自体抗肿瘤T细胞精准鉴定与冻存技术”、“飞盾eVTOL(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)”、“高分辨质谱仪工程化”等一系列尖端成果,不再是束之高阁的论文或样品,而是作为可交易、可投资的“准商品”,直接呈现在了全球客商面前。这背后,是广东省的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:让科技成果从“书架”通过广交会走向全球“货架”。
这一构想的背后,是深刻的时代必然性。当前,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加速重构,大国科技博弈日趋激烈。仅仅依靠传统的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参与国际分工,已经难以为继。发展“新质生产力”,向价值链上游攀升,成为唯一的出路。而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,正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。
广东的优势在于,它同时拥有强大的“制造能力”和不断增强的“创新能力”。据统计,广东全省90%以上的科研机构、90%以上的科研人员、90%以上的研发经费和90%以上的发明专利申请都集中在企业。这种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格局,使得科技成果转化的需求端异常旺盛。然而,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如何精准有效的服务与产业发展需求,一直是困扰产学研协同的难题,即所谓的“死亡之谷”。
广交会这一平台的介入,为跨越“死亡之谷”提供了一种极具想象力的解决方案。而这一方案能够得以实施,其最深厚的土壤和最关键的引擎,正是粤港澳大湾区。
湾区协同:独一无二的创新生态雨林
将广交会打造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沿阵地,并非偶然选择,而是植根于粤港澳大湾区独一无二的创新生态。这里“一国两制”、三个关税区、三种货币并存,制度差异带来了挑战,更催生了无可比拟的协同创新优势。
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
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明确提出,要将大湾区建设成为“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”和“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”。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,教育部、广东省等层面相继出台政策,如批准建设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(粤港澳大湾区),并从制度上保障了技术、人才、资本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。这些创新,正在逐步破解长期困扰产学研合作的“不敢转、不想转、不会转”的难题。
“科研大脑”与“制造心脏”的完美耦合
大湾区内形成了功能互补、高度协同的创新格局。香港拥有香港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,基础研究实力雄厚,是湾区的“科研大脑”。而珠三角九市,特别是广州、深圳、东莞、佛山等地,拥有全球最完善的产业集群和供应链体系之一,是湾区的“制造心脏”。“港澳+珠三角转化”的模式亦日趋成熟切独具特色。近年来,随着香港科技大学(广州)等一批港澳高校内地办学机构的落地,这种融合更加深入,实现了从源头创新到快速打样、再到大规模量产的无缝衔接。
密集的高校集群与活跃的创新主体
大湾区汇聚了中山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、暨南大学以及港澳各大高校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,形成了强大的原始创新策源地。据不完全统计,仅在各类科技成果交易会和路演大赛中,大湾区高校的项目就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,显示出极高的创新活跃度。
活跃的资本与专业的服务体系
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,为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多元化、国际化的投融资渠道,大量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积极参与早期科技项目的孵化。另外,大湾区内知识产权保护和运营体系日趋完善大圣证券,专业的法律、会计、技术转移服务机构蓬勃发展,为科技成果的估值、交易和产业化提供了全方位的专业支持。这构成了一条完整的“基础研究+技术攻关+成果转化+科技金融+人才支撑”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。
广源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